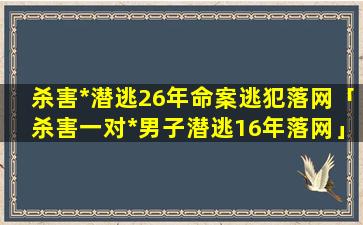杀害*潜逃26年命案逃犯落网「杀害一对*男子潜逃16年落网」
- 作者: 澜茜
- 来源: 投稿
- 2023-01-19
见到身着*、*着熟悉乡音的*,45岁的王兵(化名)忽然有种轻松的感觉:“不用再被噩梦纠缠了。”
王兵个子不高,身材精瘦,皮肤有些黝黑,跟人说话时,他的眼睛会直视对方,有时会低头陷入忏悔,有时也会露出尴尬的笑容。
过去28年,王兵都活在恐惧和忧虑里。他辗转多个省市,不敢跟别人深交,害怕别人了解自己。他频繁换着工作,改名换姓后做起了生意,年近中年才敢结婚生子。他不敢踏足自己的家乡,他说,这么多年,没睡过一天踏实觉。
17岁时,他杀了人。
2018年3月21日,已经改名换姓、结婚生子,在外潜逃了28年的王兵zui终被上海青浦警方抓获。在看守所,记者与他聊了聊。
留下一张“终于*了”的字条
▽
1990年6月14日上午,原青浦县青浦镇盈中新村发生一起故意*案,被害人卓女士及其仅三个月大的孩子遇害。
从事刑侦工作刚满一年的董毅到达现场时,小区楼下已经挤满了人。走上5楼,一个新装修不久的两居室房子里,一名年轻女子仰面倒在卫生间,身上没有伤口。走进卧室,衣橱的门敞开,里面蜷着一个刚满3个月的婴儿。母女两人都没有了呼吸。
如今墙皮斑驳的案发地所在小区,当时是新建公寓。“这家人条件挺不错的,那时候家里已经有彩色电视机了。”警方多年后回访,盈中新村的老街坊仍然印象深刻。
整座小镇都被这起凶残的*案搅动着。凶狠歹徒勒死母女的说法在坊间流传。人们在猜测凶手的动机,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被害人。
紧张的气氛也在*内部蔓延。董毅记得,为了这起案子,青浦当时总共300多名警力几乎全部出动。那几天,刑队办公室里彻夜亮着灯,烟灰缸里插满烟头,董毅和专案组同事们在烟雾中研究线索、推演案情。
“连三个月的婴儿都不放过,我们起初怀疑,这可能是一起‘仇杀’,凶手可能与死者有很深的矛盾。”引导警方往“仇杀”方向侦查的,还有留在现场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5个字:终于*了。专案组调查了死者的社会关系,没有发现可疑对象。
在凶案现场,董毅和专案组的同事提取到了一些嫌疑人留下的生物痕迹信息。受到当时技术条件的*,案发现场的痕迹和物证全靠人工进行分析、比对。
案发第三天,通过一次次的社会面走访调查和技术比对,警方锁定了嫌疑人——案发地附近一所职业高中的高一学生王兵。但当警方上门抓捕时,这个17岁的少年已经不知所踪。
他将婴儿放进了橱柜
▽
案发当天早上,王兵和另两个同学又逃课了,三个人在青浦镇上的一家桌球室里打桌球。碰巧学校的教导主任路过桌球房,但只揪住了两个学生,王兵借机跑了:“我比他们机灵”。
“不想回学校,还想再玩会儿。”王兵告诉记者,当时自己想起了前几天曾在同学的哥哥家玩连接电视的插卡式游戏机,“玩得不过瘾,还想玩。”于是他朝同学哥哥家所在的小区走去。
走上5楼,房门虚掩着。“我往里面看了下,没人。”进门后是一个餐厅,连接着客厅,王兵记得游戏机就放在电视下面的抽屉里。
卧室的门关着,王兵以为家里没人。“那个时候,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我想把游戏机占为己有。” 这个念头在王兵脑中挥之不去,他拉开电视柜的抽屉,看到那台游戏机。
就在这时,卧室的门打开了,伴随着女主人的一声惊叫。“我听到她大喊‘抓小偷抓小偷’,心里一下就慌了。”
“我想让她别喊了。”王兵说,当时“就害怕自己偷东西的事传出去”,他想捂住女主人的嘴。女主人挣脱了,跑到厨房拿了把菜刀自卫,两人发生搏斗,王兵的左手小臂受伤。情急之下,他用手绕过女主人的脖子紧紧掐住,几分钟后,女主人倒在地上。
“我也瘫坐在地上,当时不知道她是受伤还是怎么了。”为了逃避责任,爱看武侠王兵脑中突然冒出一个情节,他找了张纸,写下“终于*了”5个字。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卧室里传来婴儿的哭声。害怕哭声把邻居引来,王兵走进卧房,张望了一圈后,打开衣橱的门,把婴儿放进衣橱,关上橱门。
陷入回忆时,王兵低下头,仍觉得“当时脑中一片空白”。那之后,王兵把菜刀装进书包里,用自己的衣服擦拭了地上的血迹,逃离现场。路上,他发现没人注意他。“我就想先找个地方包扎下伤口,刀就扔在途中的经过小水沟里。”
当晚,左手小臂缠着一层白色纱布的王兵回到家中。面对父母询问,王兵脱口而出已经在心里盘算好的说辞:“我跟前两天欺负弟弟的小鬼打了一架,破了点皮。”
第二天,王兵像往常一样回到学校上课。多年后,据当年教过他的老师回忆,王兵表现淡定,远*的年龄。镇上发生凶案的消息迅速流传,同学们也在讨论。王兵消失后他的同学才想起异常:“平时他很活跃,肯定会加入谈论,但那天他异常安静,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发呆。”
“第二天到学校听同学说才知道,两个人都死了,我真的*了。”28年后,王兵再回想起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彻底完了。”他走出教室,乘坐公交直奔火车站,“扒上了一列开往长沙的火车,我想往南方逃,越远越好。”
自认“偷东西”是小事
▽
那天之前,王兵认为自己做过zui坏的事情,除了逃课、打架,就是在初中“偷了邻居家的几块钱,还被拉到*教育了。回来后,被我爸狠狠打了一顿。”
现在想来,王兵觉得小时候自己对“偷东西”这个恶习的认知“存在偏差”,“我觉得是小事情,只要读书好就可以了,没有正视这个陋习。”
在初三之前,王兵算得上是个品学兼优的孩子。小学每次考试都在班级前三,初一初二的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妈妈对我和弟弟的学习抱着很大期望,要求也严格”。
转折发生在初三那年。他迷上了看小说,看录像带,打桌球。在当时,这些都是“坏学生”做的事情,王兵的成绩随着一落千丈,中考分数只够上职高,“当时有点失落,家人也很失望。”
进入职中,王兵很快结识了几个“好兄弟”。据当年的同学回忆,身材瘦瘦小小的王兵打起架来却“很凶相”,“他一个人打两个也不一定会输。”
“父母的教育和家庭氛围都很好,是我自己没走正道。他们养育了我17年,我给他们的却是一辈子的阴霾。”回头看,王兵说人生都是被他自己毁的。
开饭店年入百万
▽
逃离上海后,王兵先后辗转躲藏湖南、广州、浙江、安徽等地。
“我有很强的求生欲。”王兵脸上露出了尴尬的笑容,无论是案发后搪塞父母的谎言,还是逃亡路上曾经几度冒出的*念头,他都“挺过来了”。
王兵将逃亡的28年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流浪”,后半部分是办了假*后的“生活”。
流浪在广州,王兵一度靠乞讨为生。有一次,走在广州火车站外的天桥上,他动过跳下去*的念头。但王兵zui终说服了自己,“也许抱着一丝侥幸,想着就算有一天被抓了,我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
捡废品、打工,流浪路上,王兵感到了身心双重的煎熬。比起身体的痛苦,每到夜晚一闭眼,那天的情景就是一个永远躲不过的噩梦,耳边响着女主人歇斯底里的“抓小偷”声。
比起黑夜,他更怕白天。“白天让我无处可藏。”他说,怕与人交流,怕秘密被人看穿,“要不停伪装,让别人觉得你是个正常人。”
1998年,王兵跟着认识的工友到西部某省做餐饮学徒。在那里,王兵用“徐涛”的名字办了一张*。有了这张*,王兵有了更强的求生*,“我*自己就叫徐涛,想跟过去一刀两断。”
他开始过起了“生活”,但生活始终伴随着噩梦和阴影。10多年里,王兵在心里说服自己“洗心革面”,为新生活打拼着。2007年,王兵来到安徽宁国,在那里跟他人合开了一家饭店,生意zui好时,每年能赚上百万元。
女儿出生让他想起被他杀害的婴儿
▽
在饭店里,王兵认识了他现在的老婆。对于结婚这件事,他一度心理很矛盾。一方面渴望拥有亲情,一方面也担心幸福随时会化为泡影。“想用亲情冲淡对*回忆的恐惧。”zui后,他还是选择了结婚,他骗老婆和岳父母,父母已经过世了,他们没有细究。”
婚后,他和妻子生了两个孩子。“大女儿出生后,我di一眼看到她时,脑子出现那个可怜婴儿,以前的画面全出来了。她越长大我越怕,我的事要是曝出来,她的一生就毁了。” 他对孩子的期待,只有让他们成为好人。“我很害怕他们学坏,害怕他们像我一样走上歪路。我不在乎他们的成绩,只要做个好人就行。”
在别人看来,王兵过着“有车有房有儿有女”的体面生活。但在别人看不到的时空里,王兵过着另一种人生。
“我老婆和岳父母都知道,这么多年我从来没在晚上12点前睡过觉。睡不着,也不敢睡。”每到夜晚,王兵的噩梦总是如影随行:“不管跑到哪里,画面总会出现在脑海里。要么梦见被害人的画面,要么梦见*来抓我了。”
被捕前一周,宁国警方通知王兵配合调查取证,提取了生物信息,那时他既害怕又心存侥幸。“害怕失去眼前的幸福,又想着也许*找错人了。”
归案后,他心里踏实了。
2018年3月21日,王兵开车准备外出时被几名*包围擒获。听到一名*用上海话说“铐起来”,他心里突然有种轻松的感觉:“所有的结果,都是我该承担的。”
落网之前,王兵也动过继续逃亡的念头。“但我还能逃到哪里去呢?就算逃得再远,也逃不出自己的心。”
“被抓后,心里踏实了。起码我可以用回父母给我起的名字,也不用在别人面前演戏和说谎了。”进看守所后,王兵全盘交代了当年杀害一对无辜母女的经过。随后,在看守所里,他体会到了28年来di一次一觉睡到天亮的滋味。
这段时间,王兵时常会复盘自己人生走过的45年岁月。他zui怀念的,是在家里的时候,跟爸爸、妈妈还有弟弟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快30年了,家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终于回来了。如果有机会,我想跟父母下跪道歉,这么多年,他们替我承受了太多。”
zui愧疚的是被害人和家属,在逃亡的28年里,王兵曾想过回来自首甚至到被害人“以死谢罪”。“如果可以用我的命换回那两条生命,我愿意。但我没脸见他们。”
来源: 上观新闻
奶牛听了庄之蝶这么说,心里倒是十分感动。但是,它没有打出个响鼻来,连耳朵和尾巴也没有动一动,只走得很慢,四条脚如灌了铅一般沉重。它听见主人和庄之蝶说话,主人说:“这牛近日有些怪了,吃得不多,奶也下来得少,每每牵了进那城门洞,它就要撑了蹄子不肯走的,好像要上屠场!”庄之蝶说:“是有什么病了吗?不能光让它下奶卖钱就不顾了它病的。”主人说:“是该看看医生的。”牛听到这儿,眼泪倒要流下来了,它确实是病了,身子乏力,不思饮食,尤其每日进城,不知怎么一进城门洞就烦躁起来,就要想起在终南山的日子。是啊,已经离开牛的族类很久很久了,它不知道它们现在做什么,那清晨起着蓝雾的山头上的梢林和河畔的水草丛里的空气是多么新鲜啊!鸟叫得多脆!水流得多清!它们不是在那里啃草,长长的舌头伸出去,那么一卷,如镰刀一样一撮嫩草就在口里了吗?然后集中了站在一个漫坡上,尽情地扭动身子,比试着各自的骨架和肌肉,打着喷嚏,发着哞叫,那长长的哞声就传到远处的崖壁上,再撞回来,满山满谷都在震响了吗?于是,从一*青草地上跑过,蚂蚱在四处飞溅,脊背上却站着一只绿嘴小鸟,同伙们抵开仗来它也不飞走吗?还有斜了尾巴拉下盆子大一堆粪来,那粪在地上不成形,像甩下的一把稀泥,柔和的太阳下热气在腾腾地冒,山地的主人就该骂了,他们还是骂难听的话吗?难听得就像他们骂自己的老婆、骂自己的儿子时那样难听吗?牛每每想到这些,才知道过去的一切全不珍惜,现在知道珍惜了,却已经过去了。它又想,当它被选中要到这个城市来,同族里的公母老幼是那样地以羡慕的眼光看它,它们围了它兜圈子撒欢,用软和*它的头,舔它的尾;它那时当然是得意的。直到现在,它们也不知在满天繁星的夜里从田野走回栏圈的路上还在如何议论它,嫉妒它,在耕作或推磨的休息时间里又是怎样地想象城市的繁华美妙吧!可是,它们哪里知道它在这里的孤独、寂寞和无名状的浮躁呢?它吃的是好料,看的是新景,新的主人也不让它耕作和驮运。但城市的空气使它窒息,这混合着烟味硫黄味脂粉味的气息,让它常常胸口发堵发呕,坚硬的水泥地面没有了潮润的新垦地的绵软,它的蹄脚已开始溃烂了。它所担心的事果然发生,力气日渐消退,性格日渐改变,它甚至怀疑肠胃起了变化。没有好的胃口,没有好的情绪,哪儿还有多少奶呢?它是恨不得每日挤下成吨的奶来,甚至想象那水龙头拧开的不是水而是它的奶,让这个城市的人都喝了变成牛,或者至少有牛的力量。但这不可能,不但它不能改变这个城市的人、这个城市的人的气氛,环境反而使它慢慢就不是牛了!试想,它在这里常常想回到山地去,如果某一日真的回去了,牛的族类将认不出它还是一个牛了,它也极可能不再适应山地的生活吧?唉唉,想到这里,这牛后悔到这个城市来了,到这个城市来并不是它的荣幸和福分,而简直是一种悲惨的遭遇和残酷的惩罚了。它几次想半夜里偷偷逃离,但新主人爱它,把它拴在她屋里,它逃离不了。当然也觉得不告诉她个原委逃离去了对不起她。可惜它不会说人话,如果会说,它要说:“让我纯粹去吃草吧,去喝生水吧!我宁愿在山地里饿死,或者宁愿让那可怕的牛虻叮死,我不愿再在这里,这城市不是牛能待的!”所以,它**地做梦,梦见了那高山流水,梦见了黑黝的树林子,梦见了那*的草地和新垦的泥土,甚至梦到它在逃离,它是在一只金钱豹来侵害城市人的时候和金钱豹作血肉之搏zui后双双力气耗尽地死去,而报答了新主人和庄之蝶对它的友好之情后,灵魂欣然从这里逃离。可夜梦醒来,它只有一颗泪珠挂在眼角,默默地叹息:我是要病了,真的要病了!——《废都》


.jpg)
.jpg)